2025年5月1日,我重温了宫崎骏的《幽灵公主》。预期中或许有怀旧的温情,但实际体验却大相径庭。
故事梗概与理性观察
客观来看,《幽灵公主》描绘了一场多方冲突:代表人类工业力量、掠夺自然资源的炼铁场;守护森林、代表古老自然的山犬族、野猪族与山兽神;被卷入其中的主角阿席达卡与幽灵公主桑;妄图夺取山兽神头颅的和尚;代表朝廷力量剥削普通民众的武士。每个派系都基于自身的立场、欲望和生存法则行动,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各方力量严重受损的结局——一种“自损八百”的必然。
作为成年观众,我并未感受到孩童时期可能体会到的那种纯粹的“好看”或冒险的乐趣。然而,也并非无聊。我的注意力自然地转向了分析:解构各个派系的动机,梳理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以及冲突带来的毁灭性后果。我能通过配乐感知到导演试图传达的无奈,主角力量在派系力量面前的挣扎,从结局中解读出对新生的希望——但这更多是一种智力层面的主题识别,而非直接的情感共鸣。我尝试“读懂”这个故事,想概括这个故事想表达的主题,最终得到的结论是我并不想强行给这个故事赋予任何主题,如果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或许代入主角的视角自然而然的享受故事才是最好的。
一个有趣的发现:理性与幻想的边界
观影过程中,一个有趣的念头浮现:我能清晰地通过理性认知到,如果我还是个孩子,我大概率会沉浸其中——我会幻想阿席达卡和桑未来的生活,憧憬自己也能与神秘的大自然有场奇遇。我会单纯的期待故事的走向,结束时还会有一些故事意犹未尽的感伤,不过这种纯粹的、代入式的幻想能力,在现在的我看来似乎已经让位于分析和解构的冲动,不过这很正常,这也似乎并不是我个人的性格特质,而是因为人总是会长大的,长大之后人就会本能的寻找所谓的电影主题和意义,不会那么天真的想象一个童话世界。
但我突然想到我玩《原神》似乎能得到孩童时代的视角,在游戏中,作为主动参与的“旅行者”,我更容易代入角色去感受故事,游戏的节奏更慢,需要我们去进行交互,游戏对角色的背景和性格特质交代的更加丰满,我们更容易体验角色的情感和旅程。这种参与感似乎能暂时关闭那个不断寻求宏大意义和逻辑结构的分析引擎,允许我更多地沉浸在当下。相比之下,作为电影的外部观察者,我的分析模式更容易被触发,去审视结构、主题和象征意义,这或许就是游戏被称为第九艺术的原因,它确实能通过更丰富的交互手段,让人抛弃观察者视角去以故事里面的角色视角来获得不同的体验。
结语
这次观影体验清晰地照见了一个转变:从孩童时期可能追求的沉浸式体验,到成年后更倾向于理性分析和意义解读。这并非优劣之分,而是认知模式随成长自然发生的变化。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与不同故事、不同媒介互动时的差异,以及为何某些体验能触动我们内心不同的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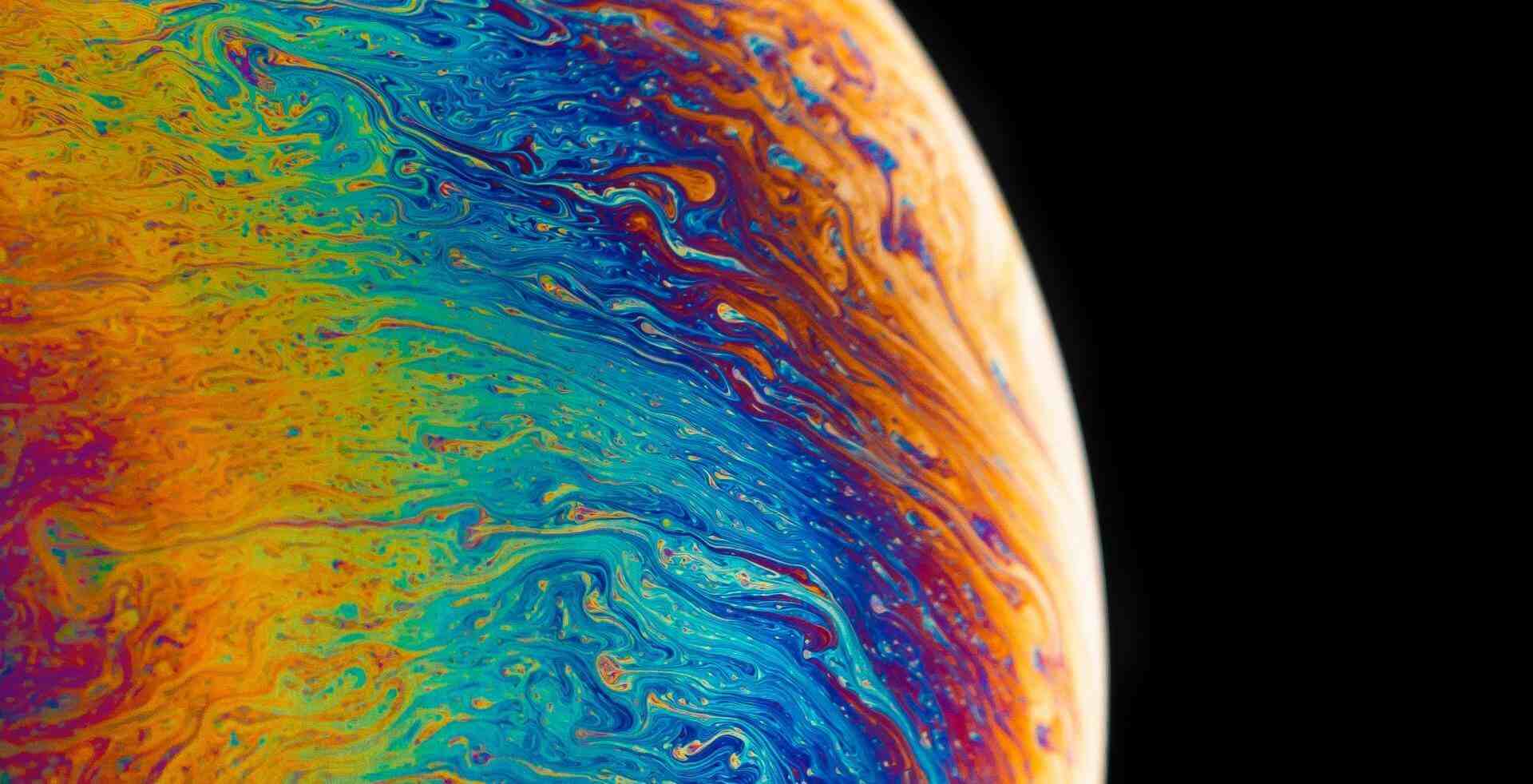
评论 (0)